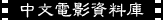抗拒沉没
--写在《露天》创刊五周年之际
邝霞
当胡钰把他的回忆文章递给我时,文名《磐石与小草》曾让我不解其意, 胡钰一解释我才明白,他指的是露天从影协中分化出来的事情。清华影协的成立是在1992年10月,当时的发起者是张岩峰、胡钰、 林朝晖等几位年级跨研二到本一的同学,在当时,影协的成立唤起了清华学子极大的热情, 三天内报名者逾四百人。后来,影协办了清华大学首届学生电影节,影评证文, 又请北影的专家教授来办讲座,一时间轰轰烈烈。
到了93年春天,影协的几位创办者又在一起议论协会如何上台阶的问题, 大家于是想到了办一份报纸。在93年4月《露天》创刊号出版了。 《露天》报的几位创始人最初的想法是把《露天》办成一份以大学生电影文化为主, 兼评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的学院式的报纸,从最初的报纸可以看到, 报上既有各类影评、名人访谈,又有文化讯息,各类文学作品(包括创作的剧本), 基本上是按照当时协会的宗旨“繁荣校园文化,提高同学审美水平”的方向来努力的。 许多志同道合者团聚在了《露天》报周围,在当时的清华可说掀起了一种电影文化的热情。 那时,有许多同学到北影读二学位,清华学子的作品在“理想杯”剧本创作大赛中还捧回了一等奖。 在后来的一年半里,随着原来的创始者陆续离开影协,影协无声无息, 而《露天》报作为大学生对电影文化、校园文化关照的产物,顽强地生存了下来, 并由原来的《露天》编辑部变成了露天社。
胡钰曾说了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,磐石是死的,小草却是有生命力的。 我想关于影协与露天的事件给我们的启示的多样的。电影是大学生独特的文化空间, 大学又给了电影独特的审视氛围,对一项艺术,热情的参与固然重要, 更离不开冷静的审视。正是这个,构成了《露天》的存在价值。
露天社作为协会成立了,除了报纸之外,又举办了许多以电影为主题的活动, 从95年的电影百年回顾展,到新年电影晚会,到德国默片回顾展, 这些活动在推动校园电影文化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至于协会组织自身, 也由原来的“露天”编辑部(以同学宿舍为据点),变成了拥有自己的办公室、 电脑、书柜的完善的协会,更可贵的是,在礼堂的协助下,我们办起了“露天剧场”, 除了能以学生的角度来为校园选择影片外,露天有了经济上自立的基础。 露天报每月的排版工作也由我们自己来完成,露天社进入了一种熟练运作的状态。
这些明显优于早期的物质基础原应该给露天带来更多好处,可是, 露天却陷入了这一切的模式之中,露天社的成员已换了四拨, 已经很少有社员能从露天的最初,从办报的初衷来思考我们的文化使命,我们的责任, 来思考露天社存在的价值。从某种意味上来说,形式已经掩盖了实质,大家看到是: 放电影--挣钱--出报纸--花钱。我想露天社最初能脱离影协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, 露天报原来团结了一批很“精神”的人,在社里他们彼此志同道合, 在真挚而牢固的友谊中,他们把报纸作为了自己的事业。他们通过协会, 得到了理解与认可,提高了自己,又把热量撒向了校园。可是现在, 我想不只是在露天社里,各种协会里这种“精神”的人都已经很少了。现在, 露天社办活动有些重量而不重质。诚然,回顾展要办,讲座要搞,可是, 如果这一切的活动没有先由大家坐下来交流,在内部对活动的形式和意义达到一定认识, 如果一次活动不能在协会内部激起反应与思考,又怎么能要求它在外面取得好的效果呢? 我们有一周一次的例会,但它更侧重于事务性的工作,仅以这种方式来举办活动很有问题的。”
作为清华唯一的一份电影文化报,《露天》报有着其它报纸无法取代的地位和无法比拟的优势。 但是,从创刊至今,露天报在风格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 从校园文化的大空间退到了电影文化,又从电影文化退到了以电影介绍为主的小影评。 文章要么是资料性、介绍性的,要么是梗概性的,感受性的,更有成为协会宣传单的趋势。 虽然报上的某些文章很有见地也很专业,但从总的来说,露天报已经失去了最初关心、 参与和创造校园文化的劲头,在关心《露天》的人们心里,《露天》报在校园文化的舞台上逐渐下沉。
要抗拒这种下沉,单从报纸上着手是远远不够的。 首先是露天社要借创刊五周之际好好地思考协会的文化使命及价值,每一个成员的责任感。 露社不能忽视自身的文化建设,哪怕是小范围内对电影、文化、生活的讨论, 《露天》的上升有赖于一个更“精神”更有凝聚力的团体。
就报纸本身,我认为有三方面值得考虑:一是内容的拓展,《露天》报不叫《电影》报, 就是因为它是包括电影在内的属于大学生的自由的心灵空间。《露天》报要以积极的态度, 创造、参与校园文化生活,反映文化动态,品评校园及至社会现象。 《露天》报能反映电影信息,但其主要功能不在于此,因为就消息的新、奇、快来说, 《露天》肯定比不上专业的、商业化的影视期刊。《露天》要反映大学生对电影的选择性。 二是影评的特色:大学生评电影是业余的、没有专家指导,没有专业知识。 但大学生有敏锐的观察力,独特的思维方式,不唯书,不唯上,只唯实的性格。 这决定了影评应该是平实而独特的。就内容来说,影评应该是包括评影片、评名人、 评电影机制、评影视文化背景的“大”影评,就风格上来说,可以是感受性的, 也应该鼓励超越电影欣赏的感性经验,对电影的抽象概念以及内在现实进行更理性的思考。 三是报纸的风格:最初的创办者曾想把它办成一份学院式的刊物, 这是有其独特的校园文化氛围的。也许我们都没有赶上高晓松反复吟唱的那个“白衣胜雪”的年代, 但他们在当时也无法体会电视、电话、网络走进学生宿舍,BBS成了校园文化的一道风景线, 信息铺天盖地涌来的巨大冲击。世界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校园也如此。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开放的世界,我们的报纸应该是把握时代脉膊,与时俱变的报纸, 应该更开放,更好地体现Openair的含义。
大一的时候,我曾经结识了许多校园歌手,校园文学爱好者。我还记得, 我曾参加过他们的一次聚会。在晚上钻进东操台阶上的一间小屋里,大家手执蜡烛, 朗诵诗歌。随着他们渐渐毕业,好像校园里能那么“精神”的人已经很少了。 现在想来,那时大家都有些Crazy,可是,那夜的烛光仍是我大学生活里最难忘的回忆之一, 连那夜的诗歌,我深深记得的有艾青的《如果我是一只鸟》,在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中, 他说:“为什么我的眼底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!”在这个出国潮涌的时代, 这首诗整个地显得有些左,但是我想,在那夜的烛光下,在场的许多人都很感动, 这种感动将作用于他们的许多选择。
似乎是离题千里了,但是,我只是想说,在这个务实、 这个潮流化的时代里, 总该有些精神的东西,存在于大学校园,存在于协会,存在我们的心中。 这种精神也许能帮助《露天》,抗拒沉没, 选择上升。
1998年3月18日
附:也许我的许多观点显得偏颇,也许我的有的愿望有些天真,我只是希望, 它们能激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,激起大家的热情。即使有人会就某一点批驳我, 我想那一定也比沉默来得好。曾经想过该退社了,已经呆了很久了, 但对于一份我深深爱着的报纸,我还是希望能再尽一份心。要知道,放弃是很容易的, 但忘记是很难的。如果你愿意,让我们坐下来谈谈,说说你的想法。 星期二晚上在这间小屋里见。